流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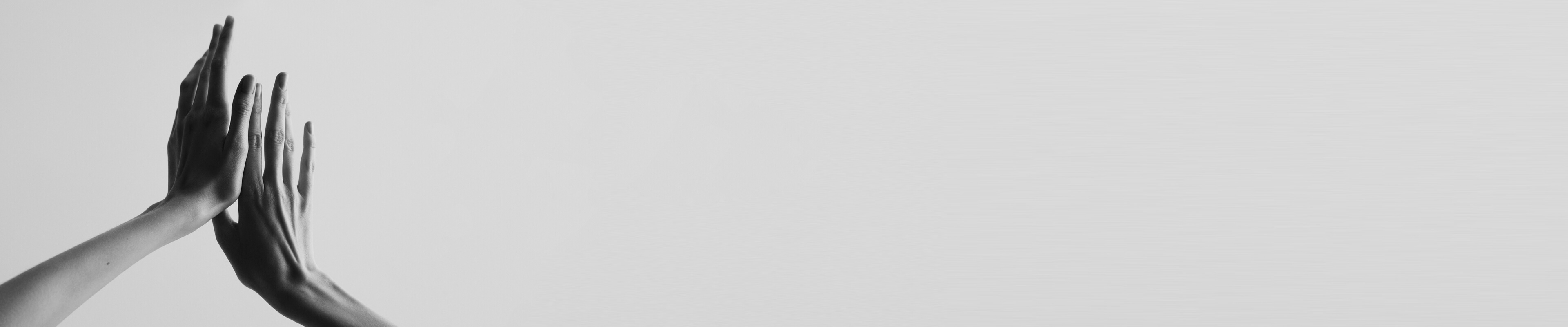
AlphaGo 与李世乭之对弈,令人工智能(AI)的话题再度热络起来。
关于人类未来的想象,一直以来有这样一种猜测:人类在与 AI 的战役中全面溃败,地球被 AI 统治,而人类沦为奴隶,甚至连奴隶也不如,因为一切人类可做之事,机器人都能更为良善地完成——人类成为地球文明的阑尾。
如若这就是结局,那也太过简单了些。
彼时的地球文明,必定依然受着外太空其他高阶文明的威胁。为使自己免于暴露,AI 并不会把依然掌握外太空广播技术的人类赶尽杀绝。人类将带着极为有限的资源,离开地球到太空流浪,寻找另一个家园。
既然是极有限的资源,就不可能将所有人类都完整地带上太空。人类将如《三体》中的云天明一样,仅留存大脑置于缸中,一排排陈列,如银行的保险柜,以伺复生之机会。尚未复生的人类,可以选择人类历史上任意一个时代,由培养缸通过电元刺激大脑皮层,产生虚拟现实(VR)之效果,使人得以如同生活在现实世界一般,遨游在历史中。这便是缸中之脑(Brain in a Vat)假设。
缸中之脑是知识论中的一个思想实验,由哲学家普特南在《理性、真理和历史》一书中提出。
我们无法证明自己是不是就是缸中之脑,恰巧选择了人类威权最为鼎盛的21世纪初来开展虚拟的生活。
我们也无法分辨,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历史上那些近乎神人的人物,是不是其他缸中之脑在我们的 VR 系统的投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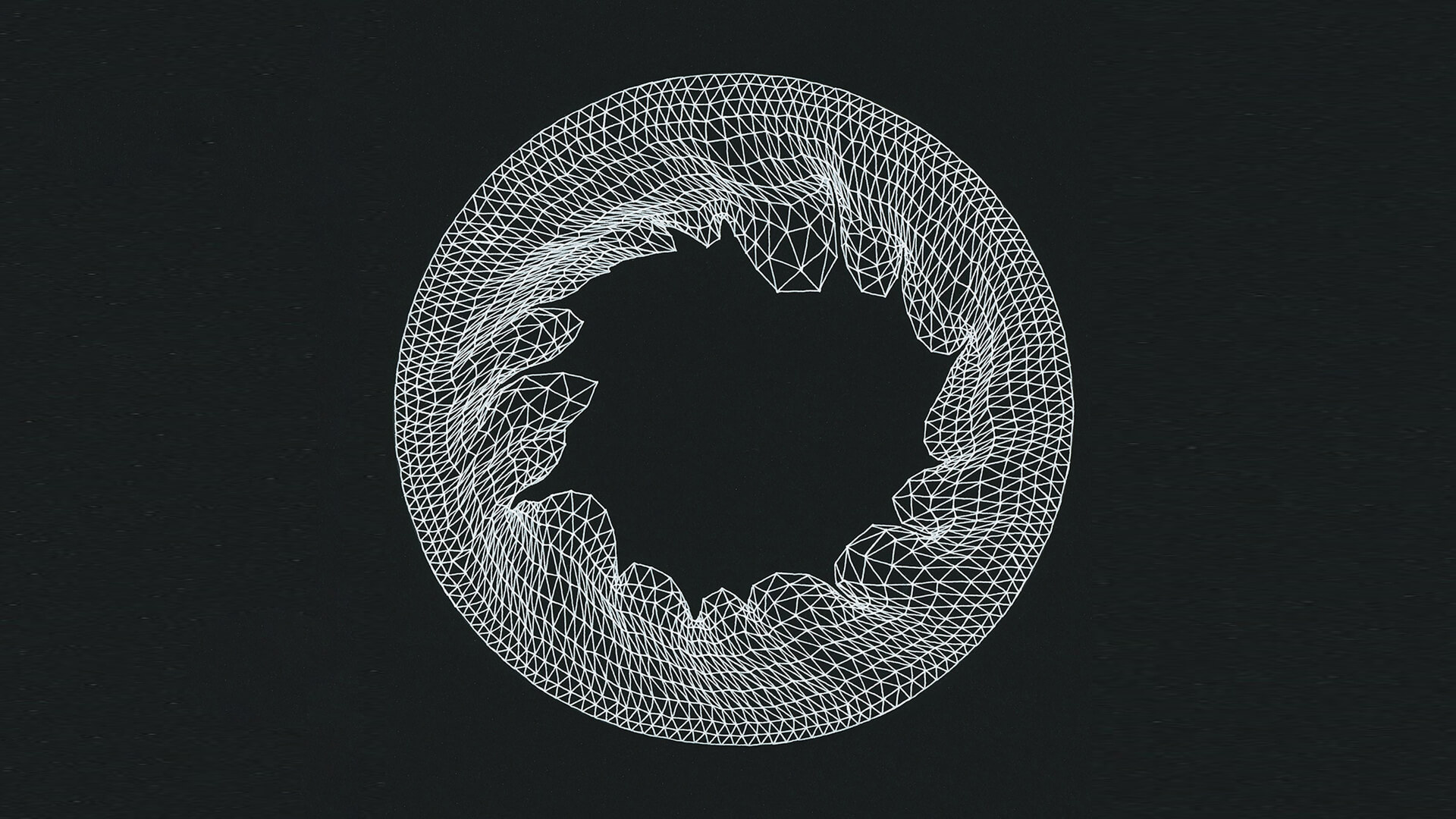
这艘承载人类未来的飞船的走向,将由少数守夜人(Night’s Watcher)来商议决定。每一届守夜人由登船前大脑的主人在人类社会的地位来决定,从各个阶层和党派中均匀选取,将他们的大脑复活,置入克隆出的躯体中。成为守夜人后,他们便要在有限的寿命中,尽力保护好整艘船,一方面要防范地球上 AI 文明随时可能反悔而派出的追兵,另一方面,又要防范外星高阶文明的搜索,毕竟毁灭一艘飞船,比使用二向箔毁灭星系要容易得多。
也许哪一天,你就会经历一次程序特意设计的车祸、空难或者海啸,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飞船之上,被带到圆桌前,和一群跟你一样懵逼的人宣读守夜人誓词:
Night gathers, and now my watch begins. It shall not end until my death……
而比《冰与火之歌》中的守夜人更惨的是,你们的背后,没有来自王庭的支持,只有 AI 文明的威胁;你们的面前,也不是异鬼这种可见真身的敌人,而是茫茫无际涯的宇宙。没有高绝的绝境长城的保护,流浪的飞船如一枚开水中颠仆的玉子,随时可能被捅破。
流浪者的心情,大概就是这样吧。
这样的感受,其实贯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全程。
那第一个走出非洲草原的人猿,是如何面对未卜的前程的?前方不再有丰饶到无需耕作便可开花结果的土地,也没有风调雨顺的怡人气候。有的是每年都要泛滥成灾吞天毁地的尼罗河,有的是寸步难行风沙狂野的戈壁滩,有的是鲸涌鲨啸巨浪滔天的太平洋,有的是万里冰封飞雪如席的格陵兰。流浪者要与气候,与猛兽,与地形斗争,方有尺寸之地寄身立命。
几千年几万年的跋涉和耕作,人类征服了五洲四海,上天揽月,下洋捉鳖,才慢慢摆脱了流浪者的标签。种群的流浪淡退,还有族群的流浪和个人的流浪。犹太人彳亍千年,才在地中海滨一隅有了自己的国家;吉普赛人至今还在各个大陆辗转求生。北京的每个地下室,都住着一个北漂的梦想;东京地铁轨道上以「捡鲔鱼」为生的人,捡起的都是自杀的人间流浪者破碎的心。
在历史中,在现实中,在 VR 中,在守夜人队伍中,无往不是流浪之地。

日神诉诸美之表象,酒神诉诸悲剧或音乐,详见尼采《悲剧的诞生》。
那么,便以尼采所谓酒神与日神之精神,共同指导我们的人生吧:
既然人生是一出戏,before the curtain falls,请让我好好演下去,而且,有声有色。
Photo Source: Benjamin Vnuk, Andy Gilmore, Daniel Trien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