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美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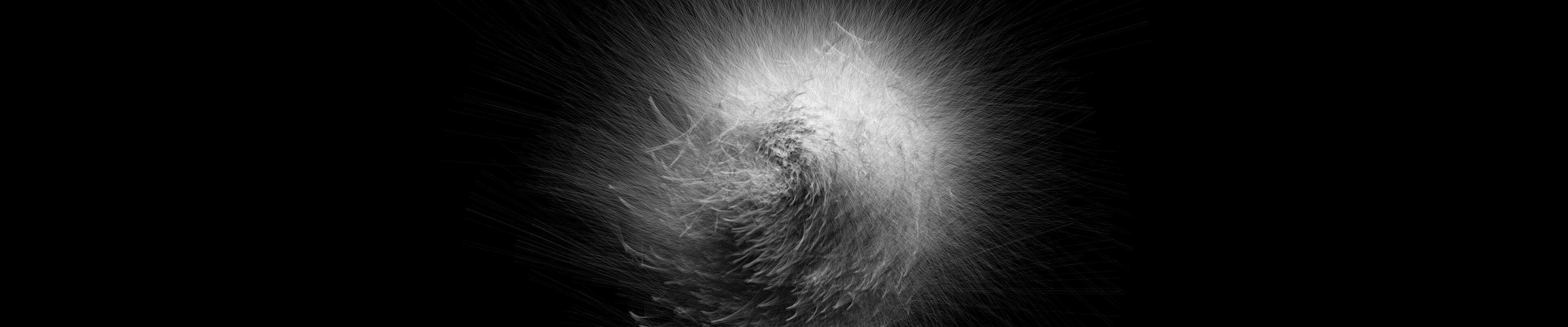
优美——古旧、原始和边缘
曾有过强烈渴望:到草原去。
自然,年幼的我所挟持的,只是种来自唐诗,来自北朝乐府的呼唤。
但,最终,我立于一片半干旱的沙地,立于黄绿的蔫萎的草中,听到导游说「这里就是阴山。」我震惊,继而悲怆。
「离离原上草」,竟是骗了我们,这些枯瘦无神的植物哪里是丰美牧草的后裔!「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也是骗了我们,天际建筑群巍峨耸峙,切开蓝空的边境。滋润过我童年与少年时代的优美诗情,在现实面前脆弱如纸。无怪乎这些伟大诗篇成了绝唱,晚近的文人对草原的种种吟咏,都不复有当年的开阔与大气——因为诗情所依附的景观已消失,因为民族的心态趋于保守,因为处在自然崩坏的末世的哀叹,永有种不祥的暗色。
《北齐书·神武纪》:「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文字上最优美瑰丽的色彩,往往来自草原这样古旧原始的边缘景观。且说这「敕勒川,阴山下」的千古绝唱,便来自北齐的武将斛律金。他是不识字的,却能在朝堂上,皇帝命他赋诗的时候,对着一朝文士冲口咏出。这样的诗,天生地造,全无斧凿痕迹,可使诸种华美炫饰的文字黯然失色。你读它,虽无直白的语句倾泻情愫,却自然觉出一种沉勇粗豪的人格,觉出万里平沙中,有一派苍茫宇宙。
此种优美激情,得益于造化,超脱于现实,是我们在日常书写中所建构的修辞传统根本无法赋予的。我们可以轻易忘记北齐的地理位置,政治沿革,忘记斛律金其人其事,忘记他的功勋与世家。但这首诗忘不掉,这首诗有魔力,它穿越使历史与人物褪色的时间,在今人耳畔鸣响。它根本不是一群文士可以凭典籍,凭格律与冷僻字建立起来的文化符号。
所以那些伟大诗篇,只从传统中袭承了一个外壳,而内里的热度,全然依赖于优美的激情,依赖于种种古旧原始的边缘景观对灵感的冲荡激发。屈原若非楚人,若非处于长江南岸的文化边地,何以兼有整饬的文辞与瑰异的想象写他不朽的咏叹?而唐王朝最飞扬的诗家天子与人间谪仙,不是戍守茫茫塞上,就是干脆生在极北极北的碎叶城。细腻、天真且孩子气的柯勒律治,自是受传统极深的熏陶渐染,可他的歌咏,绝非冶艳的闺怨,而是灿烂、大气、天马行空的古舟子之歌。即使是最最晚近的洛尔加,你若读他在纽约赋的诗,也绝不会认为爵士时代的精神给过他多少灵感。像「黑鸽子风暴」与「硬币时而呼啸成群」这样的意象,必须,也注定是安达卢西亚蛮荒瑰丽景观的纽约副本。
是的,你可以反驳,说倘使没有语法,没有词汇,乃至没有文字,这一切都不会存在,优美的激情就只是失语的咿呀。然而逻辑理性的根基,只可处于根基的位置,倘使它飞跃而上做了诗情的主宰,那结果是可怕的:情感沦为口号,沦为形式结构的附庸。胡风在广场上放歌「时间开始了」,是优美的。但经过官方阐释,经过理念的切割和硬化,就变得讨厌了。
究其原因,在于美有两端:理性之美,是崇高,是严谨依循逻辑的架构步步推移的日常建设;而感性的美,是优美,是打破传统樊笼狂飙突进,直抵人心深处的颤栗。崇高赋诗篇以外壳,优美赋诗篇以灵魂。但,对于本就以反映和塑造崇高为灵魂的诗篇,比如《浮士德》,如无优美做其灵光的底子,也必定是偏枯乏味的,必定会因为离人心太远,而成为无人问津的古旧文献。
无疑的,崇高是严肃、忧戚、有限的父亲,优美是宽和、欢悦、无限的母亲。
优美的源泉,常常是古旧原始的边缘景观。以其古旧,故可超脱日常重复的乏味;以其原始,故可引领反思反溯的思潮;以其边缘,故可与板滞强权的中央主流相抗衡。在唐诗,它是草原大漠、奇峰异岭;在中古欧洲,它是东方神话、骑士故事。如果离开文学范畴,优美的存在也有如下两种经典的表述——边缘文化对腹地文化的滋养,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冲击。

崇高——贪婪的扩张和无尽的废墟
优美诞育崇高。必是先有岩窟中的壁画,再有泥版上的文字。必是先有劳作中的口号,再有成文的史诗。必是先有伊甸园,再有赎罪禁欲的修炼。必是先有乌托邦,再有共产社会的蓝图。
法国思想家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有两套合法化的神话:其一是法国革命为代表的对于自由解放的承诺,其二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对于思辨真理的承诺。详见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悲剧在于,崇高的精神具有贪婪扩张的属性。它有侵吞优美领地的计划,更有取代优美地位的野心。且看,循着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这样的哲学链条,崇高试图建构对于思辨真理的绝对权威;再循着卢梭—罗伯斯庇尔—傅里叶—马克思这样的政治社会学链条,崇高亦试图建构对于自由解放的绝对权威。这种建构无可非议,它是崇高的根本使命所在,但建构中流露出的对于优美的忽视,不得不说是此后种种惨重牺牲的伏笔。
崇高可以驱使人民攻占巴士底狱,也可以驱使马基雅维利学说与革命蓝图勾结,驱使雅各宾派把杀人如麻当做神圣且必须的功课。崇高,可以驱使伽利略布鲁诺之徒挟科学理性斩宗教愚昧,也可以驱使科学乐观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疯狂滋长,驱使苏联政客上演《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那样的闹剧,试图炮制出一种指导一切科学与文艺的「至上的哲学」来。
详见罗蒂《哈贝马斯与利奥塔论后现代》。
怀崇高理念者,以理念完成学说进步社会转型,却也不可避免,乃至自诩正义地用理念杀人。探求原因,哈贝马斯如此归纳:「社会目标应该以合乎和谐化的兴趣的优美方式来达成,而不是远离别人的兴趣,以崇高的方式来达成。」
所谓「崇高的方式」,有票证时代长长的队伍,有广场上横流的「红海洋」,有「国家社会主义」万字旗下的焚书为注脚。它的目的可敬,手段却可鄙。而「优美的方式」,有自由市场的勃兴,文化出版界的开放,律法制度的完善为注脚。它的过程或许缓慢,结果却坚实可靠。
光阴百代,太漫漶无际了。是激情引领我们在这无际中开辟出有序。激情有两端:崇高与优美。崇高的激情带有浓烈的现实使命感,优美的激情却超脱于现实使命。摆脱,不,失去优美的崇高,可以霸占世人关于新锐,关于进步的定义,但优美未死,它藏匿于古旧和原始,伺机反击。
经院修士们编织的宗教的崇高,便遭到了文艺复兴的有力打击。文艺复兴,它假托于失活多年的希腊罗马的外壳,进行着昂扬峭拔的优美文化的建设。文化精英们编织的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崇高,亦遭到后现代主义的强势逼宫。后现代主义,它的依托就更原始,只是人的混沌意志,只是对一切冠冕堂皇话语的本能的反动。但恰是这种以古旧对抗新锐,以混沌对抗秩序的方式,带来了世俗社会与个性解放,带来了优美在思维场域的回归。
崇高的无尽废墟,证明这不是古旧、原始与边缘的胜利,而是人性对抗非人性的胜利。
可是优美的最大敌人,不是崇高。恰恰是在优美荫庇下成长的世俗,使优美濒于死亡,无奈远去。

世俗——日已中天,挽歌不远
世俗化本是祛除神魅的大业,却在二十世纪急转直下,演化出物欲化消费主义的可憎面目。
优美不是就此消失,它在这里被打碎重组,成为物欲化的自我包装、自我合法化的工具。直观、赤裸裸的物欲,依然是有悖于基本的道德伦常的,于是它假托优美的外壳,把物欲精神化,把消费审美化。世俗之低空与崇高之长天,亵渎之沟渠与神圣之峰巅,便奇妙地得到假象式的统一。
你以为你感受到的是优美,实际上根本不是。它只是优美的碎片,而潜入意识的是物欲。正如同你以为你得到过穆斯的垂青,实际上根本不是。医学报告会告诉你,起作用的是流进你血液的安非他明。
我们这时代,不是不能生出第二个梵·高,但这些梵·高第二的种子,常常深陷于来得太容易的名声,深陷于广告美学与画廊营销术的商业化泥潭。这个时代的荷马,在苦心孤诣地炮制献给权利的颂歌;这个时代的伊壁鸠鲁,在声嘶力竭地宣传着某某药物的神效;这个时代的莎士比亚,已然明白了把故事冲淡调稀成洋洋数百集肥皂大剧的伎俩;这个时代的巴赫,更懂得用破碎却悦耳的乐句来招徕听众短暂、浮躁而多金的猎奇心。
优美的源泉——那些古旧原始的边缘景观,亦在消失中。产出不敌标准化机耕田的草原,开垦之;长势不如廉价次生林的原始森林,砍伐之;揽钱不敌人气大商圈的故居,拆除之;销量不及显学畅销读物的巨著,雪藏之。
可是,尽管优美远去,它从未消失。优美,以其宽和博大的母性,占据着后发制人的优势。崇高的锋锐无所不在时,优美隐蔽了;但崇高崩坏,受人唾弃的时候,如果没有优美的《九三年》与《日瓦戈医生》,没有优美的《自由引导人民》与《春风已经苏醒》,谁会怀念崇高?谁能怀着平和客观,乃至有些悲悯的情感,去发掘崇高的价值?是优美,是优美扮演了墓前致辞的角色,为曾经狂热过的崇高留下一个抒情性的总结。
当下的世俗化物质主义,有着不亚于崇高的锐利锋芒。是的,优美确乎不是短程角斗的胜者,它确乎无奈地远去了。但物质主义绝无绵延千载的生命力,因它不是人类最高级的希求,它的一切伎俩都只是暂时的蒙蔽。
要淡然地目送优美的远去,因为它必会归来,必会在归来后为崩溃的世俗化的物欲作一篇优美且温暖的墓前致辞。
Photo Source: Mark Nystrom, George Desipris, Jezael Melgo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