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的白色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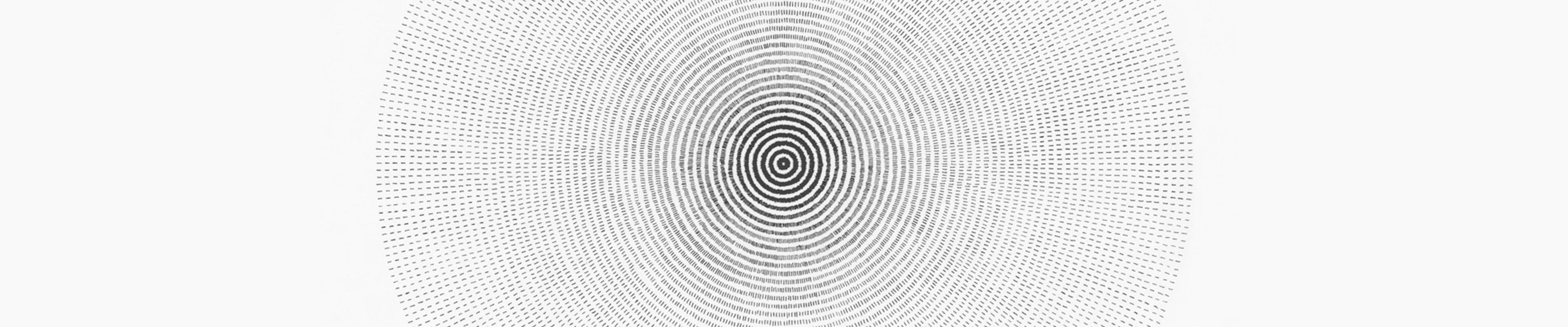
要开做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阿垅《无题》
「要开做一枝白色花」,这是阿垅在诗里的说法。然而按照当时的境况,他不是「要」,而是「只能」「开做一枝白色花」。这里面有环境的压迫,但更有诗人自己的选择。不然,他为何要用「要」这样富有个人意愿的字眼呢?
他要的是什么?「开做一枝白色花。」这愿望在今日看来太微小,在当时已属殊不易。为何不能是彩色的花?因为彩色有罪,彩色象征多元,丰富,自由,是专政所不允许的。于是他选择了白色,纯净而无辜,用以表现自己真实的品质。他的愿望也并非成为白色的代表投降的旗子,白色的充满死寂的蟒纸,而是花朵,作为生物繁殖链条上的闪光点的花朵,这就使得他的看似微小的愿望里充盈着生的张力,美的光弧。
阿垅为什么要开做一枝花?「因为」,他用这二字毫无滞碍地引出心声;「我」,他大胆地脱离那个「我们」的语境,用自己的声音来庄严地「宣告」:「我们无罪。」
这个宣告是惊人的。这个「我们」囊括了太多和他一样蒙冤受屈的人。这个「无罪」推翻了太多千奇百怪的罪状名目。这枝白色花正释放着惊人的力量,来洗涤同类身上乌有的垢污。
然后呢?「然后我们凋谢。」刚刚因欣悦而升腾的情感骤然熄灭。一枝白色花的宣告再如何庄严,都会被一个以宪法为一纸空文的时代轻易判决为无效。阿垅知道自己代表了美善的一角,也知道丑恶是如何嚣张而有力,故他选择了凋谢这种抵抗的方式。这种方式虽为激进者所不齿,但要知道,那个时期一切恢复「人」的权利的条件都极不成熟,一个怀着火种的普罗米修士的力量过于渺小。而凋谢,恰可以于无声中控诉高压政治的摧残,也因为他可以诗意地「凋谢」而作恶者必将丑陋地「暴毙」,便有了于精神上俯视作恶者的效果。他是自己选择的死亡,故使以他的死为乐的人丧失了邪恶的快乐。
也正是因为他的凋谢,今天的我们依然能从诗中读出并记住他的那枝白色花。在他之后的许多诗人走出了那个时代,生长成了彩色的花,获得了物质丰裕所馈赠的贪婪,庸俗,假清高,甚至卑鄙,也就再也没有那样的庄严,那样的纯真来宣告「我们无罪」。
白色花已绝版,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Photo Source: Cyril Galmi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