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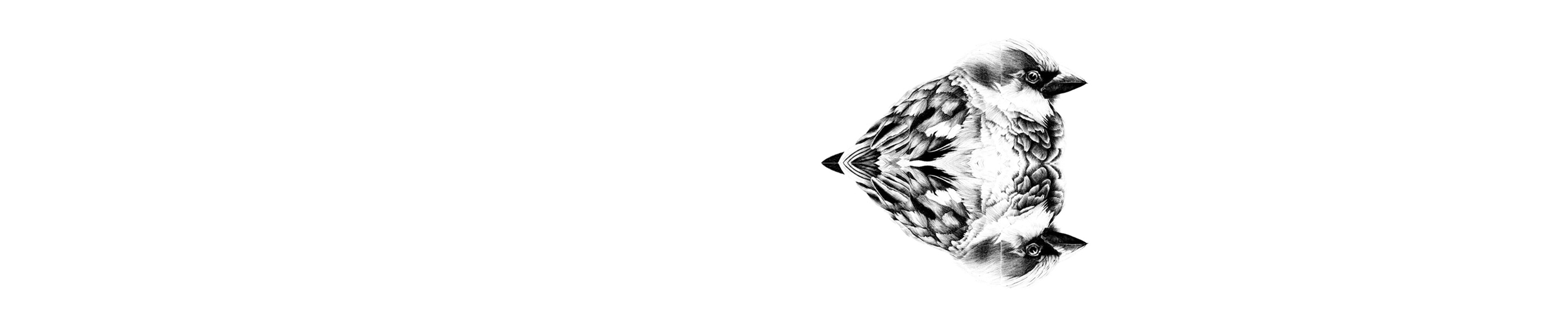
麻雀是江南常见的鸟类。
它们是填补于我所居的这个小镇的缝隙的边角料,是潜藏在市声中的一组难听的拗格,是三三两两零零落落永不成气候的一群。它们的颜色是没有名字的颜色,斑纹是失去章法的斑纹,模样是转瞬即忘的模样。那褐色大约是它们的本体,卑微而无定,那灰色则是小镇的符号,是它们与灰色的天空、云雾、烟、烟囱、厂房、民居与居民共同佩戴的袖章。
麻雀是没有灵气的鸟类,不比鸽子的机敏而缄默。它们莽莽撞撞地闯进灰的河流灰的房子灰的人灰的故事,再急急忙忙逃出去,鬼鬼祟祟聚起来,把碎片化的故事拉扯成它们自己也听不懂的流言。那些流言是小镇隐形的肌骨,悄悄把自己纺织着,穿针引线着,绣出一种叫做命运的织物来。
永和豆浆
永和豆浆不知何时落户在街拐角那片店面。小镇上人气的流转向来对浮躁的商人秘而不宣。麻雀逐剩菜而居,却有这样的天赋,纷纷栖落在电线上,俯瞰招牌下黑的白的戴帽的戴盔的脑袋蜂拥而至。清早叽叽喳喳声里,店员热情的宣誓开启一整天的好生意。
我在那里遇见徐,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
她是我小学同学,她在永和豆浆当服务员,她应当知道九月中旬所有高中职校都已经开学,她辍学了。
辍学的变化是显然的——她也学会了穿小一码的牛仔裤,她也学会了在乏味的工作服上钉一排亮片,她也会把枯干的头发烫成微卷,她也会把指甲涂成杏红。
但她终是和那些简单爽辣的女店员有所区别。她一直低着头,如拘谨的小兽物。我这才注意到她脸上的痣已扩大成斑。不知道会不会癌变,若真会,她恐来不及享用完苦涩的短暂青春,和青春以后的悠长的清淡。
于是我忽而感到愧疚起来。我忽而想起她的小小悲剧里有我的戏份,那是个夜晚,月明星稀,我对着她的朋友说出我转述的第一句流言:「徐不是她爸妈亲生的。」这恐怕称不上是种愧疚,我的诚恳不够,更像是种倨傲的怜悯。
麻雀在这时飞到店后头闲置的自行车库顶上,看店员偷偷摸摸搬运两大袋豆浆粉。又飞近,看徐倚在窗口,在手机屏幕上敲下一行表情符号。那一排笑脸,是披挂上薄薄外装的极淡极淡的忧伤。
桥弄里
桥弄里是这座小镇的记忆源头,是永字八法的第一笔,是王谢燕宿的乌衣巷口,是外来人口的理想栖居。无处不是黛瓦灰墙,那灰是灶火的洗礼,是造纸厂废气的吻痕。无处不是残垣断壁,缝隙里隐隐透出外来者飘萍般轻的家什。无处不是吵吵嚷嚷的小孩,追逐着麻雀,不知道何为疲惫,只觉着家里玩具太少。
我坐在理发店里看老板娘给孩子洗澡。应该是接近尾声,玩具鸭子已经被玩腻。老板娘的手伸向干毛巾,确认没有碎头发干扰后,把孩子一扶,一捞,一放,仔仔细细擦干。小袜小帽小衣服虽然略旧,但补丁的针脚平和整饬。然后她叫我坐下,扫开地上的头发,用一种初为人母的温和细致,在我头顶上认真誊写一份规整的学生发式。
理发店毗邻外婆的娘家,小时候常来。年久失修,物件都显出些年月。墙上的海报先是落后于潮流,再是蒙尘积灰,终成今天这副泛黄卷边模样。发式老旧,故来的都是常客。而好些年纪大的客人都相继辞世,生意就日渐冷清起来。镜子里有另一个理发店,她的脸在其中虽不显得漂亮,略略胖了些,鼻翼两侧有斑,却也温柔可爱,有母性的光泽。我知道这是个背井离乡寻求生路,为着孩子能吃上安全的奶粉而劳累的母亲。
店员接手她手里的活,一时无事可做的她就靠着镜面,蘸着热水在上面作画。她是在画脸上没有斑存折里有好多零孩子有无尽的奶粉和玩具的另一个自己吗?
「囝囝快来哎!别让被子上落了麻雀粪!」老太太在外边叫着。孩子跑出去赶麻雀,不多时定又是一身汗。正处好动年纪的孩子,一天洗两回澡,无碍。
架着衣被的竹竿一头靠着房檐,一头搭在桥边栏杆上。那座桥后来拆了,新桥距此很远,光滑平整,没有可以晾衣服的栏杆。那家理发店,我再没去过。
听说,从麻雀那儿听说,他们迁走了。
茶叶蛋
茶叶蛋在安静地泡温泉。
水泡从底下上浮,胀大,触及水面的瞬间结束生命,化作氤氲的热气。茶叶蛋只是被动地一颤,复归于安静,仿佛只有如此安静,才能波澜不惊地从寡味的白煮蛋变成醇香的美味。
卖茶叶蛋的婆婆是熟悉的人。每年都如此,在冷冷的冬日里兀自推着小车煮着茶叶蛋。她头发已经花白,不是那种安逸富贵的银白。身上的棉袄蓝不蓝灰不灰,过于老旧,处处起球,她也不去掐掉。
「她的儿子或者女儿不在新年里给她买新棉袄吗?」
「嘘,小孩子不要瞎说话。」
于是我知道婆婆的子女不孝,又或者,婆婆并没有子女。麻雀一定知道婆婆的故事,这时候它们都不见了。大约是因为它们中有一只在婆婆肩头新遗下一点湿湿的麻雀粪,自感羞惭了。
她捞起一勺茶叶蛋,只有一个是煮坏了的,拧着脸格外黑。蛋上,和婆婆脸上一样,定是用了国画里最最凌乱的一种皴法瞎劈了一通,估计还在赭石色里泡过。她把那只蛋捏手里,端详一番,在衣角上擦擦放进口袋,不卖。其余的蛋都个大饱满,爬满了精致细密的裂纹,剥开来一定是光润美丽,像是刚长成的青年。
我不知为什么想要吃那只坏的蛋。她先是一愣,尔后徐徐拿出来递给我。
果然不好吃。我吐出来,把残余的随手扔掉。
婆婆像是有话要说,终究没说出。她肩头的麻雀粪干了。
我想,那茶叶蛋真像婆婆。她应该是苦苦养育出了一帮不孝的子女,他们把她涂了一身的麻雀粪,再像我这样随手扔了。
有一年冬天,卖茶叶蛋的婆婆没有来。
请试着用一种麻雀的角度俯瞰这座小镇,古运河与京沪线从中穿过,水泥灰的房屋铺展开来。你能看到洗头的船女,打牌的船工和运不完的煤炭铁矿砖石,也能看到招手的游子,怅惘的旅人和载不尽的钢材木料石灰。河流是灰的绸缎,枕木是灰的花瓣,烟囱里徐徐吐出的是灰的炽热。这炽热有红色的眼睛金色的梦,是狂热破灭前的欢欣。这欢欣是没有顾虑的,它扩张着膨胀着直至爆炸,留下伤疤。而她们,是这伤疤的终点站。她们用宁静悠久的生活平复创伤,还命运一个普通的微笑。
你会觉得这小镇的俯视图像极了一张挂着普通的微笑的脸。它看到的是过往的人物,预示的是我们的未来。谁能读懂这普通背后的隐秘?谁能参透这微笑背后的忧伤?麻雀呼啦啦飞过,它们是江南的魂灵的碎片,是她们的冷漠的知音,是绣像上传神的眼睛。
我央求麻雀告诉我更多故事,它回头,茫然地扫过我的脸,一如扫过那些故事主人公的笑和泪,然后回过去,毫无情感地,扑棱棱飞走了。
Photo Source: Ewa Prończuk-Kuzi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