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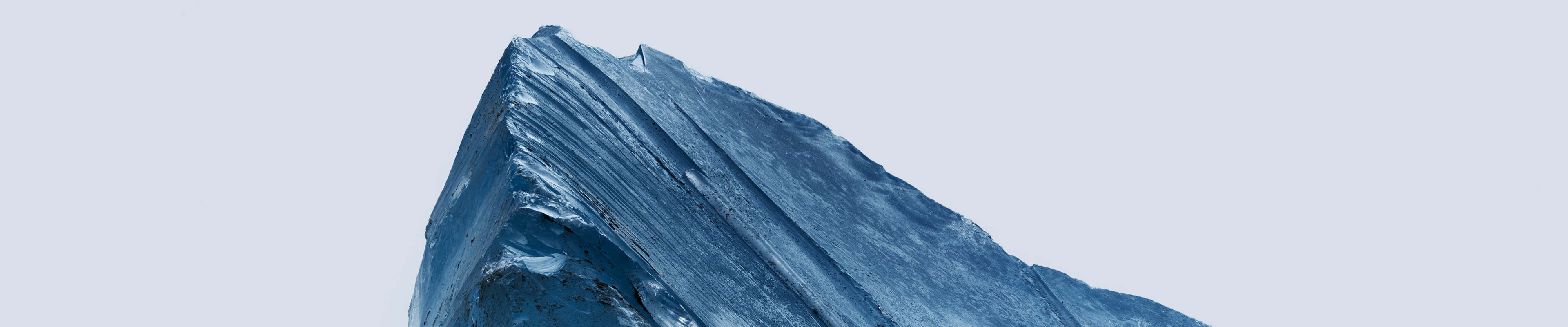
梦是液态的黑。沉沉,像有铅雾坠下去,又透明,像有刀光斫开来。
混沌。
有了光,分开明暗。
有了气,聚沉为陆。
有了声,是鼓点,遥无际涯。
有了味,是节日,富丽丰饶。
循着路走,虽不知一片暗中何者为路。光点变大,成了斑,再近一些,张开斑驳颜色。尔后,斑斓同温煦搅拌发酵,催开馥郁,令人应接不暇。
地上有方的冰,抱在怀里,不化。暗红灯火星星点点,勾勒欲醒之睡城。天空由靛青变浅紫,变绯红,转牙白,定格于湛蓝。喧嚷市声醒来,节日彩旗醒来,肃穆廊柱醒来,伟大意志醒来。
有人告诉我,是冰凌节。
有人盛给我一盏冰,清润如玉,经久不化。他说异邦人,快来欣赏我们的节日。橙花和木瓜香气沿他手中铜勺注入冰盏。
有人唱着诗,言辞古奥,情真意切。他说异邦人,快来加入宏大的歌颂。长幔和华冕托走迎接帝王的行伍。
我怀抱方冰,走近唤我名字的老妇。她推着盛满冰凌的木车,周身铺满孩童的无忧之乐。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认得这里全部的异邦人。
这里又是什么国度。
是一片四面环海的黄金般的大陆。
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来参加本国最盛大的节日。
是纪念谁人的节日。
不,不是纪念,是歌颂伟大的帝王,当今的统治者。他用神威驱散黑雾,他用神恩播撒禾黍,他用神德教化万户。
冰凌也是这里的物产吗。
不,它来自凌人所居之北地。凌人以巨船载来不化之冰,同我们换取食品、布匹、油料和金器。
凌人是什么人。
是哲学家的后裔。哲学家是帝王之前的统治者。那个时代富庶繁华。但哲学家无计控制人心之日益腐化。于是帝王出世,放逐他们。帝王教我们使用武器,开拓疆界,服从官吏。于是我们明白:没有无瑕之人心,犹可有不输往日之繁华。
但我并未看到这里有腐化之人心。
噢,异邦人,你在此地待的时间太短。你不知道这块大陆如今正以什么作支撑。帝王慈爱,顽石放光;帝王震怒,河断海枯。帝王权力至高无上,帝国子民愚鲁无知。市政广场再无辩者,学堂诵经皆非贤人。这里只准有一种思想,万鸟只能发一种声音,百花只准开一般颜色,千帆只可朝一个航向。
但我所耳闻目见的一切,皆如是丰富绚烂,并无你所言的喑哑暗沉。
这是我们少数人坚守之结晶。哲学家赐予音乐,我们不辍弦歌;哲学家赐予诗篇,我们不废吟哦;哲学家赐予画笔,我们落笔成斑斓春色;哲学家赐予刻刀,我们挥手成累累秋实。帝王威严不可鞭及,他亦不复以此为意。高压之统治早已招致不满,他的疏忽终将惹来一场灾祸。
作为异邦人,我不宜多问,但请让我知道,这是何等灾祸。此地万物美丽可人,却要面临潜在危机。我会听,即使我不忍。
噢,我对你吐露的已经太多,再说下去,恐要泄露天机,那是我担不起的责任。你来此地是有重要使命,连你自己也不知的使命。可是不用疑惑,朝市政广场走去,你会在那里找到答案,在那一刻面临抉择。
推冰凌车的老妇消失在节日人潮。
市政广场坐落于都城南部。人群因钟声警告收敛节日之喧阗。随默然大众朝南方步行,稀疏耳语令我得知众人是去观摩帝王处决一批重要犯人。
宏丽廊柱朝南方广延,绚烂花木盘旋在台阶重重之碧泉。贵族金玉遍身,与素服布鞋之平民一同垂头虔敬地赶赴王辇所在。他们神色全是羔羊意态,唯有我不知礼数向四周张望窗台。
窗口掠过一张忧郁脸庞。她的肃穆平抑了本会泛滥而失衡的悲哀。像是新月不忍天上落寞下来做她的眉,像是珍珠难捱海底岑寂渡来当她的眼。像是云霞忘记落日召唤跑来染她两颊红晕,像是玫瑰听从花蕾心声攀来画她润泽樱唇。忧郁面庞转瞬即逝,余下海藻般长发的剪影同卫兵粗暴的呵斥。人群里传过一个声音,她是凌人首领遗腹的女儿,今日处决的头号犯人。
市政广场早早架起高台,如林圆木捆绑火把。冰凌木车往来吱哑,清凉甘甜把观众的急切暂时压下。
喧腾众人霎然静寂,重叠金幔驾临此地。戍卫长矛伸展如穹顶,盖不住煌煌如焰,是帝王威仪。 他迈着不可一世的步伐登上高台,他用上傲视一切的目光横扫子民。他扶扶夸张冶艳的华丽冠冕,他整整虚荣浮华的锦绣霓裳。
今天,是开国第一个千年的冰凌节。我将在此,与万民共见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犯下劫掠残杀我帝国子民之重罪的凌人全族,将在光明的火光里悉数灰飞烟灭。
我看到帝王肥大舌头像蛆虫蠕动,我望见犯人青紫瘀斑像毒蛇紧缠。我遇上凌人无辜眼神,纯净如冰。我听到凌人自述,揭穿浮华言辞矫饰的谎言。
我们是凌人,是哲学家的末裔,是流亡北地的孤魂。
我们的先祖开辟鸿蒙,造地上天园。遍授种作织造冶铸之法,广教文史算演音画之则。
我们的人民日趋败落,深受魔鬼蛊惑。魔鬼化身金光闪耀之帝王,用巫术将先祖驱下宝座。
我们在那苦寒北地忍受无涯孤独,用澄明智慧铸造不化之冰。再以巨船载至此地,才有冰凌节。可是帝王又以含毒之芳花蜜果当冰凌的点缀,冰凌便不能立即使子民开启心智。但我们别无他法,只能让这冰更澄明不化。帝王便教那毒花更鲜妍,毒蜜更甘醇。如此斗争,已有千年。
今日,本该是斗争终止,万民启智的日子。但帝王用诡计,将前来和谈的凌人皇族全部扣押,到北地大肆屠杀戮灭全族。帝王的罪孽如此深重,他的报应势必接踵而来。可怜这些愚鲁草民,因顺纵腐化之私欲而要当他的陪葬。
她,那张忧郁脸庞,是先王之女。她继承了父亲的深沉大智,却没有继承他的谨慎周全。她的失策绝非她的过错,而是无耻的帝王手段太残忍。
审判的时刻就在今天,美玉与恶石一同焚灭。身担重任的异邦人,快用心听听她的声音。
凌人已然被绑上刑柱,败草枯柴在燃烧中慢慢变成香木。凌人冰一般纯净的身体升腾成烟,不留下供人凌辱的残破尸体。
节日的氛围越发浓烈,食过冰凌的人民丧失理智。他们忘情地起立欢呼,覆灭的预兆是青烟盘旋在天际的火山口湖。
她的眼睛像暗里强光,箭一般锐利地穿透心骨。她的嘱托饱含着炽烈的愤怒,那愤怒沿着目光喷涌而出。

怀里抱着的方冰剧烈融化,内核透出一柄锥子的模样。我攥紧它刨开昏热的人潮,刹那间已跃上帝王的高台。
刺客。
是的,我是。
但你不是凌人。
我的心,已是凌人的心。
本以为把他们杀尽,就没有这一天。
但杀不尽的,唯有心。
我没有罪恶。
你在说谎。
锥子推进帝王的胸膛,他用临死的力量把冠冕戴在我头上。骚动的人群居然恢复了平静,用崇敬的眼神告诉我,我是他们新的帝王。
魔鬼的声音隐约可辨,他要我与他订约。出卖你的好灵魂,你会成为这国度永恒的主上。
人潮里骤然现出冰凌车老妇那双眼,她用不可质疑的口气告诉我:
知道你为什么能听懂凌人的言语?要知道哲学家只用眼神和心声交谈。告诉所有人,你是最后的凌人。
于是金色冠冕打碎在地,逃出一阵烟一样黑色的魂。我扯下不知何时已披挂在身的锦袍,对着人群失控地咆哮:
快醒醒啊,沉睡的众人!你们的大陆正因你们的罪孽而下沉!
复苏的火山会烟蔽千里,炽热的岩浆会夷灭万城!
看,那些坚守着智慧的子民,他们生出了翅膀,把他们带向希望的日出之东方。
看,这些执着于丑恶的罪人,大地张开了沟壑,让他们葬身绝望的日落之西方。
作出你们的抉择!我已无话可说。我再也帮不了你们,我只是最后的凌人。
醒是固态的白。清澈,让人两眼生疼,又寒冷,催人忘却昨夜的梦境。
可是我忘不掉,翻开地图,追寻大西洋里那片沉没的大陆。我的手指穿越北纬三十度,游历所有曾经灿烂的今日的废墟。然后,落泪。
我是最后的凌人。
Photo Source: Jonathan Sager, Tjitske Oosterholt